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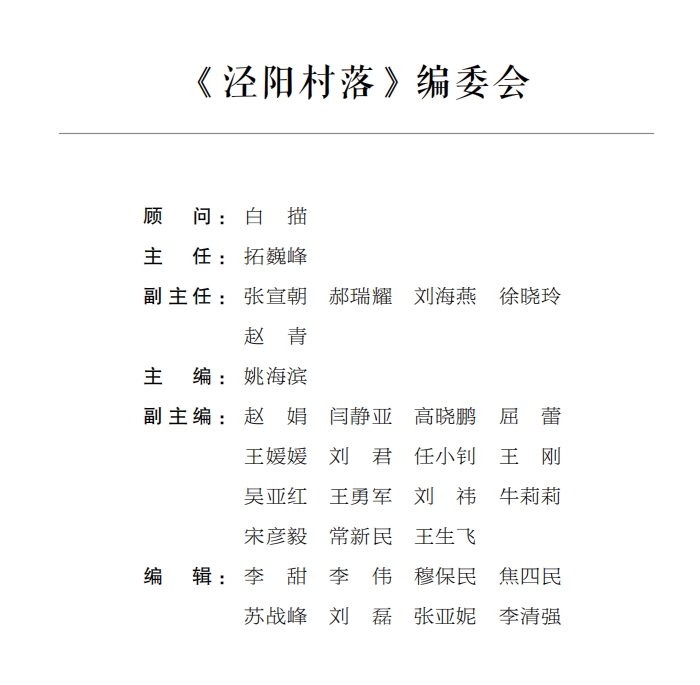
梦里河湾河南村
文 川
在泾阳县域的最北端,古老的冶峪河从嵯峨和仲山间的谷口夺路而出,在泾河北岸的黄土台塬上凿出一道深约百米的开阔峡谷。峡谷的左手是渐次抬升的斜坡地,右手是壁立的土崖,土崖之上便是平整开阔的西城塬。

▲金色河南村
大致在数百乃至千年之前,或因一场旷日持久的连阴雨,或因一场强烈的地震,峡谷中段右岸的塬崖发生了一次大规模坍塌。从高处落下的土方所携带的强大动能将位于塬下的河床向北推送200多米,在塬崖与河床间堆起一片近300亩的台地。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竟将这方台地开垦成农田,做了养家糊口的依靠,还在台地的最高处建起小小的村庄。这其中就有我那迄今已传至八代的杨氏先祖。也许这里曾经有陈姓和田姓人定居繁衍,也留下了陈家沟和田圪崂的旧名。如今,这里属口镇郭垣村一个村民小组,并依地理位置取名“河南村”。
小村背依黄土台塬,前有小河环绕,得河水灌溉之利,算得上一块旱涝保收的风水佳地。借此,我的先辈们大抵都过着相对殷实的日子,也曾出现过家业繁盛和人丁兴旺。
人口增加带来的是生存的挑战。眼见得河湾的百余亩水浇地已不足以养活小村的百余人口,先辈们只得把目光投向村后塬头上的旱坡地。他们或用省吃俭用的节余从邻村的败落之家购买,或带上一家老小披荆斩棘,将多年撂荒的塬坡地重新开垦。就这样,多年以后,小村的住户终于在村后的塬头上经营出了一块近300亩靠天吃饭的旱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在那场靠精神的力量激发起来的“改天换地”运动中,一条跨越山涧、绕过山腰的人工石渠建成通水,昔日汩汩东流的河水第一次改变了自然流向,流进了塬头那未曾浇灌过的农田,浇灌出一个时代人们对旱涝无虞的期盼。在接踵而至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我的父辈们冬战严寒,夏斗酷暑,用几乎最原始的工具,将昔日的斜坡地修成平整的水浇地。在之后的岁月里,无论这些土地的使用权属如何变迁,但不争的事实是,这些土地成为村民们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也是村民心中最稳固的依靠。
不能忘记小时候我的父辈们每天出工必须攀爬的那道塬坡。仰角超过30度,晴天积出厚厚一层尘土,雨天变成没过脚踝的淤泥,只将空架子车拉到地头便能耗尽一个人的全部体力,更别说进地干活了。适应这一艰苦的生产条件,村民们大都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秉性。长期以来,村中绝少游手好闲的懒汉。老人们即便到了七八十岁的暮年,依旧会种几分地,养几只羊,捡几根柴火。他们不是在为生计奔波,他们的劳作只是一种习惯,一种农村人所特有的惯性。
大约在民国年间,有人出于好奇尝试引进了大蒜种植。不曾想,当地特殊的土壤和水质竟然成就了辛辣爽口的河下紫皮大蒜品牌,成为当地农户最直接的经济收入来源。
最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几位不安于现状的生产队干部突发奇想,大胆决策,利用邻近河水的便利,延请山东师傅开办起集体所有的粉条加工厂,组织社员利用冬季农闲时间,低价收购塬区普遍种植的红薯,加工成粉条出售。此举既增加了集体收入,提高了劳动日值,又改善了村民生活,引来周围各村的羡慕。
在随后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村民们凭着从山东师傅那儿学到的手艺,家家户户从事红薯加工和粉条生产,成为享誉一方的粉条加工专业村,有几家甚至成为当地最早一批“万元户”。而就在那几年,我的父母正是靠着粉条加工的获利为在外求学的我提供了相对充足的学费和生活保障。
机缘巧合的是,邻近崖塬的地理位置让小村的地下水含有一种特殊的盐碱成分。用本村的井水加工的粉条看起来更透亮,口感也更筋道,成为享誉一方的乡土品牌。
时至今日,尽管当地塬区已不再大面积种植红薯,更无法满足粉条加工的需要,但每到红薯收获季节,村里从事粉条加工的人家还是要远赴百里之外的周至、鄠邑、大荔,乃至三门峡一带收购红薯,运回加工,使人们口口相传的那缕舌尖上的记忆得以永久保存。
在城市化进程席卷神州的新形势下,小村和它周围的同伴一起渐渐地老去。摆脱了对土地依赖的年轻一代象南飞的孔雀般离开农村,涌进城市,只有那些垂暮之年的老人们长久地围坐在村口的大树下,固守着记忆中的家园。
小村,孕育了我们生命,记录着我的童年,颐养着我的父母,是我心中永远的牵挂,是我魂牵梦绕的故园!
作者简介
杨东峰,笔名文川,泾阳县作协常务副主席
(本文选自泾阳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2022年10月编辑出版的《泾阳村落》第一辑)
责任编辑:王顺利/《新西部》杂志 · 新西部网